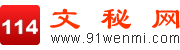【www.chuban323.com--剖析】
论文内容提要:目前,关于都市新移民的研究中,市民化与本土化两个视角都比较强调现有的制度与文化对移民群体的同化以及相互间的融合,也带有比较强的政治色彩。而从“移民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上述两个视角所研究的在上海的农民工与台商两个移民群体的比较发现,如果把“移民化”理解为当地社会与移民群体之间的同化与融合,那么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则是一种“反移民化”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下而上的渐进式社会转型所形成的“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社会变迁路径可以对上述现象作出解释。在此基础上,一种“群体性共存”的“移民化”新模式开始形成。目前,关于都市新移民的研究当中,有两个新的视角,一个是从“市民化”的角度关注进城农民工与征地农民的权利获得(陈映芳,2003;文军等,2004;林拓,2004);另一个是从“本土化”的角度关注台商在大陆的状况(耿曙,2002、2003;黄凯政,2004;林家煌,2004)。其中,前者更多的是从公民权的角度出发,探讨进城农民工与征地农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后者则更多的是在海峡两岸政治结构的框架下面,探讨台商的本土化是否会导致中国台湾地区产业的空心化,以及两岸的经贸联系最终是否会影响到政治格局的变动。严格来讲,这两个概念都带有很强的政治关怀。在本文的研究当中,将利用更具有社会学味道、更加中性化的“移民化”的概念来对上述两种视角进行整合,并对他们所研究的进城农民工与大陆台商两个群体进行比较研究。
从“移民化”的角度来看,上述两个研究视角都比较强调当地现有的制度与文化对移民群体的同化以及相互之间的融合。其中关于市民化的讨论比较倾向于从城市市民现有的权利与生活方式出发,讨论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距离,并由此出发来讨论农民工的未来发展问题;而关于本土化的讨论则比较倾向于关注台商企业在当地的经营状况、台商与当地人的社会交往状况、以及他们对当地社会的认同状况。本文,在关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农民工和大陆台商的研究中发现,随着移民进入都市时间的增长,随着移民群体规模的扩大,我们看到的不是“移民化”的程度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表现出“反移民化”的倾向。
对于这种现象,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没有进行充分的关注。本文的研究将从对此现象的考察出发,从“结构-制度分析”着手深入讨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外来人口“移民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并在此基础上对“移民化”的概念作进一步的探讨。
农民工与台商的“反移民化”倾向
在上海都市新移民的调查当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早期进入上海的移民,包括农民工和台商,往往都要经历一个非常痛苦而漫长的逐步适应地社会生活的过程。他们往往不但要努力学会当地的方言,而且要尽量要求自己按照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来看问题,努力在当地人的夹缝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们也会尽量争取与当地人进行更多的交流。但是对于后期进入上海的移民来讲,由于早期的移民已经为他们在这个城市中争取到了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在当地人的夹缝中谋求生存:他们努力争取尽快融入当地社会的动力大大下降,他们不但不会去学当地的方言,甚至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也更愿意固守自己传统的东西;在社会交往方面,这些后期移民也表现出日趋封闭的倾向。
从同化与融合的角度来理解,本文的“反移民化”倾向实际上包含了两重含义:一是指“移民化”的结果,即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移民化”过程,新移民变得不是越来越像当地人,或者与当地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是变得越来越不像当地人,与当地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二是指“移民化”的过程,即在“移民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不是一种同化与融合的趋势,而是一种分化与隔离的倾向。具体来讲,这种“反移民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移民变得越来越不像当地人。这一点,对于农民工来讲,可能更多的可以从收入差距上出来。在过去的这些年中,虽然农民工的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权益(包括社会保障与子女入学等)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总体来讲,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虽然对于生活方式与观念方面的改变,还没有很好的指标来测量;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民工群体来讲,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近距离与处于高收入水平群体的接触对观念的影响,有时候产生的可能不是一种认同,而是一种仇视。对于大陆台商来讲,问题的表现可能正好相反,虽然近几年,台商与上海当地人之间在收入差距上日渐缩小,但是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却在扩大。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地区的服务业入住上海,台商适应上海、融入上海的动力开始下降。
其次,新移民的行为方式日益非正式化。对于早期移民来讲,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往往要求助于当地的公共机构或者政府部门。但是对于后期的移民来讲,由于他们的先辈们已经开创出了一套穿透正式体制与制度的行为方式与非正式渠道,他们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式或渠道很快地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通过正式的方式或渠道来解决问题逐渐失去了兴趣,至少已经没有太大的动力去争取。
第三,新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日益封闭。对于早期的移民来讲,他们为了在城市中立稳脚跟,不得不与当地人打交道,并在与当地人的交往当中建立起自己的支持网络;虽然这种网络很脆弱,或者让人很不舒服。但是随着移民群体的不断壮大,移民之间的社会支持体系变得越来越庞大,新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往往呈现出一个日益封闭的倾向。
对于上述现象,本文的经验调查主要来自于对不同移民个案的深入访谈,在访谈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早期移民与近期移民生活状况的差异,以及早期移民在“移民化”过程中生活状况的变化。③
对“反移民化”倾向的“结构——制度”分析
在“移民化”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出现逐步“同化”与不断“融合”呢?在调查中发现,与早期移民相比,近期移民进入当地社会时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少了,已经没有早期移民那种处处碰壁的感觉;与早期移民相比,近期移民对于当地的那种陌生感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他们已经在当地生活得比较舒服了。对于那些老移民来讲,近期与早期的这种差异更是明显。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这些移民已经逐步被当地所同化,或者与当地逐步实现融合了呢?进一步调查发现,事情远远不是如此简单。
以往的制度与文化体系变得日益开放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以往的制度与文化体系之外的新的社会空间的快速成长。在调查中发现,近期移民之所以觉得进入当地社会的障碍越来越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些移民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套解决各种问题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体系,他们基本上不再需要去哪怕已经开放的制度和文化体系当中寻找支持了。在移民比较集中的区域,移民文化甚至逐渐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而当地人则逐渐成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比如,被台商称为“小台北”的昆山,按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柏兰芝教授的观点,已经形成了台商与当地政府之间的“跨界治理”。[1]也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才使得移民化过程表现出来的不是当地人对外来人口的同化和相互之间的融合,而是相互之间的分化与隔离。
为什么“移民化”的过程会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呢?这很大程度上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市移民政策的变动路径相关。建国之后,城市的移民政策曾经经历过一个由开放到封闭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我们经历了一个把帝国主义的在华企业和侨民逐步排挤出去的过程,这个过程,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称为“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谢艾伦,1996/2004)对内,我们也经历了一个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并逐步封闭的过程,这一点,在关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研究中也有了很详细的讨论(陆益龙,2003)。但是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这种从开放到封闭的过程都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建构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制度变迁先于结构变迁,制度建构结构”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城市移民问题上实际经历了与建国初期正好相反的过程,也就是说,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我们都又经历了一个从封闭逐步走向开放的过程。但是由于我们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渐进式”道路,所以与建国初期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经历的是一个“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过程。
在这样的社会变迁逻辑下,当移民进入城市,面对一个封闭的城市体系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时候,他们发现,在原有的社会体系之外,重塑一套新的社会结构要比改变原来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要容易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早期移民在不断从原有的社会体系与制度缝隙中寻求资源的同时,开始把越来越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在体制外建立新的结构与空间,当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和空间逐渐形成的时候,不但老的移民会逐步把自己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支持体系建立在这些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空间之上,而且会成为新移民们创业的乐园;老的移民会逐渐失去向旧体制进行挑战的激情和动力,而新移民可能连这方面的欲望也没有了。于是在“移民化”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反移民化”的倾向。
当然,对于本文所研究的农民工与台商来讲,这样一个社会变迁的逻辑,在具体运行过程中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对农民工来讲,这种“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过程,更多可能是一种被动和无奈的过程。因为他们是都市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从最初的“在夹缝中生存”,逐步沦为城市社会的最低层。从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进城以来,已经有1亿多人口以这种身份生活在城市当中,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已经在城市中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但是在我们的话语体系当中,他们仍然是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中存在的合理性还仅仅在于我们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他们,我们城市中的一些脏乱差、危险的工作和服务离不开他们。直到最近,才逐渐有一些学者开始从公民权的角度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城市才开始在法律法规上要求企业为农民工提供“三金”,为民工子女提供同样的教育;全国总工会也开始考虑农民工进入工会的问题。
对台商来讲,虽然他们不是都市化中的弱势群体,但是他们对于正式制度的态度与农民工有些相似。台商往往面临两个方面的制约:一个方面来自台湾当局,他们的很多限制使得大陆方面为台商提供的一些方便措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来自实际的执行部门,虽然大陆方面对台商制定了非常优惠和宽松的政策,但由于两岸关系的敏感性,使得实际的工作部门在处理涉及台湾事务的时候都非常的谨慎,在这种情况下,一道道无形的障碍就被设定在台商与我们的城市当中,使得台商们不得不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台商的圈子当中。
在调查中,有很多准备在大陆长期发展的台商,看好上海未来的发展前景,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在上海发展,因此他们计划让自己的孩子更早地进入当地学校接受教育。但是事情的结果常常不如所愿,大陆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压力往往让这些台湾孩子难以适应,最终的结果往往还是逐步从当地的学校中退出来,或者回台湾,或者进入上海的国际学校就读。
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进入上海,他们逐渐在上海形成了自己的移民群体,并在古北路、仙霞路等地区逐渐形成了台湾人比较集中的社区。新来的台湾人,一旦进入这个环境,就如同回到了台北。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与早期移民相比,已经感到方便了很多,并且在进入上海之后,也不再有那种很强烈的陌生感;但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与当地居民形成了比较密切的互动关系,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当地人的融合又进了一层。
对早期的移民来讲,他们在大陆创业、投资,要想成功,就必须依靠当地人的力量,通过学习上海话、交上海朋友种种途径来使自己变得更加像一个上海人。但是对新来的移民来讲,由于有了早期移民的基本信息和基本的支持,仅仅在这个社区的内部就能够把自己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差不多了,因此,也就失去了与当地社会进一步融合的动力。 这样一种“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社会变迁模式,不但使得我们的“移民化”过程表现出“反移民化”的倾向,而且会使得我们的“移民化”过程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的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社会变迁中的“锁闭”效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在他的经典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曾经专门论述了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问题。在诺思那里,正式制度的变迁由于受到更为稳定的非正式制度的制约而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2]在中国“自下而上”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过程中,早期阶段,“路径依赖”更多的表现是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制约作用,但是到了后期,日益成熟和完善的非正式制度体系会逐渐把我们的制度变迁过程锁定在这样一种自发形成的结构当中,从而出现诺思所讲的“锁闭”效应。
目前,在农民工与大陆台商这两个移民群体当中,“锁闭”效应已经初见端倪。庞大的农民工移民群体以及“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使得我们的城市在做出任何让步的时候都表现得谨小慎微,因为城市的管理者不知道一个小小的制度修正的背后,到底会涉及多少人命运的改变;因为不清楚,一个小小的制度修正的背后,到底会带来多少相关政策的连锁反应。反过来,那些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也早已从那种一步登天的幻想中解脱出来,对于城市给予他们的积极反应已经有些麻木了。对他们来讲,变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城市人已经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与其寄希望于城市人偶尔施舍,还不如把精力更多地置于移民群体中,经营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
对台商来讲,这种“锁闭”效应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是我们开始以一种“服务”的姿态讨论“两新”组织的党建问题,其中包括台湾人集中居住的社区和台商的企业。对于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由“非弱势群体”移民形成的社会结构,已经不是他们要求与当地社会进行同化和融合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正式组织和结构开始想办法如何进入他们当中。
这种“锁闭”效应可以说是目前关于移民问题进行新的制度建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当这些外来人口已经在我们的城市结构当中逐步稳定下来、并逐渐形成自己比较独立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的时候,且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和制度体系已经以“习惯”的方式稳定地存在于移民群体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当地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可能应该考虑的已经不是如何从自身的标准出发来改造他们,而是要进行自我调整,逐步把这些结构与制度纳入新的社会结构与制度体系当中。
“移民化”与新的移民模式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我们的城市在重新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经历的是一个“结构变迁先于制度变迁,结构型塑制度”的路径,因此,在农民工和台商这两个外来群体“移民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就不是一种与当地社会逐步同化与融合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实现与当地社会“群体性共存”的过程。本文在开始部分所描述的这种“反移民化”的倾向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移民化”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面,“移民化”实际上是新的移民不断地争取与当地社会享有平等的“群体性共存”权利的过程。
当然,这样一种“群体性共存”关系,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文化上多元共存的关系,还带有很强的社会分层的蕴涵。也就是说,新形成的移民群体与当地的社会结构之间,包括不同的新移民群体之间,已经逐渐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层分化的倾向。这种等级分化结构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了当地社会与移民群体之间,以及不同的移民群体之间的一种再结构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直接体现了这些移民群体“移民化”程度的加强。
注释:
① 本文的初稿曾经于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中国城市研究网2004年12月12-14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的“中国城市:城市研究的新一代”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周雪光教授对本文发表了主题评论,另外,本文的研究得到了美国纽约州奥尔巴尼中国城市研究网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文仍然存在的所有问题及相关的责任将由作者本人承担。
② 本文中的“台商”,指中国台湾地区在大陆经商(包括投资建厂和从事贸易)的人士。
③ 在上述的比较研究中,我们需要控制的一个变量是早期移民与近期移民的一个差异,即早期移民已经经历了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访谈的早期移民来讲,经过了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沉淀下来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移民的特征;但是对于近期移民来讲,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在经历了自然选择的过程之后可能最终会选择离开。应该说本文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中,并没有对这个变量进行很好的控制,但是考虑到本文所考察的问题与这个变量发挥的作用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变量发挥作用,在本文的调查当中应该发现的是与本文论述的正好相反的逻辑,所以,不控制这个变量对本文的结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柏兰芝、潘毅. 跨界治理:台资参与昆山制度创新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座,2003. 9. 19
[2]诺思,刘守英译.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上海:三联书店,1994
参考书目:
(1)陈映芳. 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调查.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2)耿曙. “资讯人”抑或“台湾人”?——大上海地区高科技台商的国家认同. 佛光大学“第二屆政治与资讯研讨会”﹐2002
(3)耿曙. 连缀社群﹕WTO背景下两岸民间互动的分析概念. 许光泰﹑方孝谦﹑陈永生编. 世贸组织与两岸发展. 台北﹕政大国关中心,2003
(4)黄凯政. 大陆台商当地化经营之研究——以大上海地区为例.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
(5)林家煌. 过门不入:大陆台商信任結构、协力网络与产业群聚.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论文大纲,2004
(6)林拓. 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与农民市民化.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编. 城市研究简讯第11期,2004
(7)陆益龙. 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文军等. “农民市民化”问题讨论专题.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编. 城市研究简讯第12期,2004
(9)谢艾伦,张平等译. 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深度剖析香港问题 深度剖析自己 深度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深度剖析摩羯座(下篇) 深度剖析属猴摩羯男 月亮狮子座的深度剖析 月亮巨蟹座的深度剖析 月亮白羊女的深度剖析土地确权无地农民咋办 无地农民补偿申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