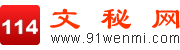【www.chuban323.com--法律论文】
宪法解释的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
——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为中心的宪法解释方法考察
刘飞
【学科分类】宪法学
【出处】《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摘要】应以何种方法来解释宪法,是中国宪法学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宪法解释方法的考察可知,解释主体综合运用各种解释规则所形成的规则综合模式构成了传统的解释与推论模式中所谓的解释方法,但实际上确定宪法解释结论的是注重解释结论实体正当性的结果取向,而规则综合模式起到的仅是论证解释结论的作用。宪法解释方法是一个融汇解释规则适用与结果取向于一体的过程模式,规则综合模式在个案中的具体确定需要以基于结果取向的解释结论为依托,而结果取向对于解释结论的决定作用也被限定在规则综合模式所容许的范围之内。中国宪法的现行立法解释模式具备实现解释结论实体正当性之制度基础,但应加强解释规则层面上的论证。
【关键词】解释方法;解释原则;规则综合模式;结果取向
【写作年份】2011年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宪法解释问题日益为我国学界所关注,而宪法解释方法虽在一定程度上仍被视为技术层面的“末技”,但亦有学者称之为“现代宪法解释学中核心的问题”[1]。研究宪法解释方法的成果并非罕见,但多以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宪法解释理论与实践为学术背景,论述所及则通常限于对各种解释规则作具体描述。对于不同解释规则在宪法解释中的相互关系如何、解释规则在解释结论形成过程中具有何种实质意义、解释规则与结果取向之间的关系如何等问题,往往语焉不详。实际上,我国的宪法解释权主要集中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体制上迥异于以美国模式为蓝本的“分散、具体的违宪审查制度”,而与源自欧洲大陆的“集中、抽象违宪审查制度”更为接近,因此至少应给予后者的释宪经验以同样的重视。[2]作为“当代抽象、集中审查制度之典范”[3],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近六十年的司法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宪法解释方法理论也堪称蔚为大观,对之作深入考察,应有益于尚缺乏释宪实践的我国。而在我国现行宪法所预设的立法解释模式基础上,着力研究如何借鉴与我国近现代法制建设颇具亲缘性的大陆法系国家的释宪经验,则更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德国法语境中,通常认为宪法解释是对于基本法规范意义内涵的探求与确定。黑塞曾试图对宪法解释作出更为精准的界定,他认为举凡宪法的具体适用都可以被称为是宪法的实现(Aktualisierung),而只有那些致力于解决宪法疑问的具体适用才是宪法解释。[4]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因为宪法的实现和宪法解释之间的界限实在无从划定。对此,黑塞本人也无法否定至少从广义上而言可以将宪法的具体适用认定为是宪法解释的观点。[5]在此意义上而言,则有权作出宪法解释的机构还包括行政机关、其他法院以及宪法机构。本文之所以需要依托联邦宪法法院来考察宪法解释方法,是因为唯有其作出的宪法解释才是最终和最权威的,可以起到主导性解释的作用(Interpretationsherrschaft),而其他机构作出的宪法解释则充其量仅为“辅助性渊源(Hilfsquellen)”而已。[6]
宪法的基本任务是在一段尽可能长的时期内确定国家的基本法律秩序,因此其必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以适应未来的发展。为此,宪法规范往往首先表现为是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规范,而未见得是严格司法技术意义上的规范,例如基本法第1条第1款中所谓的“人的尊严”和第21条第2款中所称的“危害联邦德国的存在”等。从另一方面而言,宪法规范是对国家基本法律秩序作出的根本性规定。作为“约束政治和公权力行使的规范和标准”[7],宪法规范直接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等诸多难以作出明确具体规定的敏感领域,因此其不可能是完整的、封闭的和无漏洞的,而只能是“少量的、部分而言简明扼要的和不完整的”[8]。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基本法中确实包含有少量明确具体的规范,但其多数规范属于所谓的“框架性秩序(Rahmenordnung)”,而并不具有确定的规范内容。[9]因此,宪法规范中必然存在着较大的解释空间,其对于解释的需求明显要大于在规范内容上更为详细具体的其他规范。而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宪法乃是人们基于一定时期内的智识水平和现实需求所确定下来的规范,其对制定规范之时的现状作出的回应本身就有可能是不充分的,更何况其还需要担当包容未来发展之重任。因此,宪法“不能适当回应其未预见的问题,乃至使国家不能有效处理新的挑战,殆属不可避免;宪法与‘国家理性(Staatsraison)’间会发生冲突,本可预期”。[10]
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宪法规范文本的稳定性,但却使之部分丧失了规范的周延性。为使抽象规范能够对接于具体实践,同时避免作为“政治法”的宪法规范及其中的较大解释空间为各种政治力量所肆意操控,学者们长期以来致力于研究如何获取解释结论的理性过程,而宪法解释方法的探求无疑是其中的核心问题。然而毕竟宪法规范具有其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如果完全拘泥于追求方法论意义上的技术性和逻辑性的完善,又未见得能够解决现实中的具体宪法问题。而与此同时,由于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具有普遍性的拘束力[11],因此如果法院不能在解释方法上作出严谨说明和论证的话,其裁判的正当性往往会受到质疑,进而损害法院的权威性。为此,应当“依据尽可能严格的学术标准和客观标准,按照批评性的、透明的和可被事后验证的准则”[12]来作出宪法解释。这一目标是否能够达成以及可以在何种程度上达成,就成为了宪法解释方法讨论中的核心命题。
二、解释规则
学界通常将可以同时适用于宪法和其他法律的解释规则称为“一般解释方法”,联邦宪法法院则称之为“用于解释一般规范和宪法规范所采用的方法”[13]。早在1960年,联邦宪法法院第二审判庭就对此作出了明确阐述:
根据“主观说”,解释的基础是“立法者”在历史上的意愿、即其在当时环境下的动机;而根据“客观说”,解释的对象就是法律本身、即立法者在法律中被客观化了的意愿。“客观说”在司法实践和学术讨论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正如拉德布鲁赫在《法哲学》一书里所说的,“国家意愿并不是通过参与立法者的个人意见来表达的,而是通过法律文本来表达的。立法者的意愿集中表现为法律的意愿”。
服务于此解释目标的有根据规范的文义作出的解释(文义解释)、根据规范之间的相互联系作出的解释(体系解释)、根据规范的目的作出的解释(目的解释)以及根据法律材料与法律的形成史作出的解释(历史解释)。
为探求立法者的客观意图,所有的这些解释方法都是可以采取的。各种方法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14]
以此裁判为基础,可以把宪法解释区分为探求宪法客观本意或主观本意的两大类方法,此即所谓的客观解释和主观解释。客观解释的重点在于确定宪法文本的文义内容,主观解释的重点在于探求立法者的立法本意,而目前学界达成的共识则是“应以客观解释为基础”[15]。具体而言,宪法解释基本方法主要有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和历史解释四种,即所谓的“经典四方法(vier klassische Auslegungs-methoden)”。其中,除了文义解释为公认的首要方法之外,其他各种解释方法之间并无严格的适用顺序。联邦宪法法院仅仅在其裁判中明确表示过“法官应同时运用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以作为文义解释的补充”[16],但却并没有明确各种解释方法之间的具体界限及其适用顺序。事实上,要在各种解释方法之间划定明确的界限是非常困难的。例如目的解释的基础就是规范的文本,因此难以把目的解释与文义解释截然分开,而体系解释同样也需要以文义、目的和历史等要素为基础。由此看来,客观解释和主观解释之间似乎并不能形成明确的界限。
从文献中的用语来看,多将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和历史解释称为“一般解释方法”,或称之为解释法则(Auslegunsgcanonen)、解释要素(Element)、解释标准(Auslegungskriterien)等。严格而言,这些所谓的“一般解释方法”不过是解释过程中必须要予以考虑的基本要素而已。之所以称之为“一般”,是因为其不仅存在于宪法解释之中,在一般法律解释中亦如此。但宪法解释的“方法”却并非仅限于对这些基本要素的运用。换言之,“解释要素”并非“解释方法”之全部内容,因此不能将“解释要素”等同于“解释方法”。正如萨维尼曾明确指出的,这些所谓的方法“并不是解释的分类,而是一个单一解释过程中的要素”[17]。为此,本文将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和历史解释等称为“解释要素”。
萨维尼之后,仍有学者主张宪法解释方法应当限于上述解释要素的运用。[18]而更多学者为突出宪法解释的特殊性,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总结出了专门适用于宪法解释的各种原则,诸如宪法的统一性原则(Einheit der Verfassung)、实际协调原则(Prinzip der praktischen Konkordanz)、功能正确性原则(Prinzipder funktionellen Richtigkeit)、整合效力原则(Prinzip der integrierenden Wirkung)、宪法的规范性效力原则(Prinzip der normativen Kraft der Verfassung)、合宪解释原则(verfassungskonforme Auslegung)等。[19]其中,宪法统一性原则被视为宪法解释中的“首要原则(vornehmstes Interpretationsprinzip)”。由于“宪法的本质在于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确立一个统一的规范”[20],因此宪法解释与一般法律解释之间的区别之处在于:其不仅对于法律制度中的部分领域、而是同时对于整体意义上的法律秩序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欲使宪法承担起规范整个法律制度的功能,就必须把宪法理解为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innere Ein-heit der Verfassung)的规则体系。换言之,“不能孤立地考量一个具体的宪法规范,也不能仅仅基于该规范来作出解释。单个具体的宪法规范在意义上与其他宪法规范一道构成一个整体,宪法本身则构成一个内在的统一体”。[21]然而即便仅就解释技术而言,所谓的“统一性原则”似乎同样也存在于一般法律解释之中,例如对民法典某条文作出的解释同时也应当顾及其他相关条文乃至于整体意义上的法典。
相对于解释要素而言,解释原则进一步考虑到了宪法规范的特性,尤其是宪法规范中所体现的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分配和整合国家权力等目标。但是,这些原则实际上不过是在宪法解释中如何具体适用各种解释要素的指引、综合或导向而已。例如宪法统一性原则、实际协调原则、功能正确性原则和整合效力原则,实质上都是要求在作出宪法解释时应当顾及其他相关宪法规范的意义以及宪法在整体上所体现的精神,因此博肯菲尔德指出,其不过是体系解释在宪法解释中的具体表述而已。[22]基于同样的原因,也有学者直接把这些原则归类到体系解释之中。[23]而宪法的规范性效力原则与文义解释多有契合之处。至于合宪解释,其根本渊源又在于宪法统一性原则。因此从整体上而言,所谓的解释原则并不能够完全独立于解释要素,而不过是“针对宪法在规范结构、规范对象、规范功能和适用条件等方面的特点对于一般解释方法(解释要素)作出的强调而已”[24]。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尽管宪法解释问题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即被视为法律解释中的特殊问题,但其与一般法律解释之间除了受政治的影响程度不同之外,在适用解释规则方面并无根本差异。[25]因为,“宪法首先也是法律,因此在解释方法上不应将宪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作原则上的区分”[26]。或许正因如此,联邦宪法法院在宪法解释中通常都是并用解释要素和解释原则,而并不刻意在两者之间作出区分。对于宪法解释中所适用的这两类基本规则,文献中一般统称为宪法解释方法(Methoden der Verfassungsauslegung),本文则称之为解释规则。
三、规则综合模式
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联邦宪法法院不能依据单一的解释规则作出解释,但在通常情况下,法院都会在裁判中综合运用各种解释规则。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法院在个案中适用不同的规则,其形成解释结论的推论过程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也很有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解释结论。如果此假设能够成立的话,问题的关键似乎就在于法院如何选取解释规则并确定其适用顺序了。而如果能够如此确定解释规则的适用模式的话,则不仅可以增强解释结论的可预测性,法的安定性原则也得到了实现。然而基本法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在主要是对法院的程序性事项作出规定的联邦宪法法院法和联邦宪法法院议事规程中,同样未见有相关规定。那么,可否期望通过多年判例的积累来达成上述目标呢?从联邦宪法法院近六十年的司法实践中,似乎也看不出有此迹象。之所以如此,有可能是因为联邦宪法法院极少在裁判中明示其所适用的解释规则,以至于人们难以通过判例中有关解释规则的阐释来总结其适用规律。但实际上即便是在法院对解释规则做出了明确说明的那些判例中,其具体解释过程的内在结构和各种规则的适用条件亦不甚清楚。因此尽管我们可以设想解释规则在一定意义上限定了联邦宪法法院的解释方式,但是联邦宪法法院在选择和具体运用解释规则上还是拥有较大裁量权。并且法院究竟是如何运用这一裁量权的,仍然还处于不明的状态,这就是恩吉斯所谓的解释学说中的“最具争议性的问题(umstrittenste Frage) ”[27],而考夫曼则称之为法学方法论中的“根本问题(Kardinalproblem)”[28]。
对于联邦宪法法院在解释方法上作出的阐释,马伦霍尔茨教授认为其“前后并不一致”[29]。而曾任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的伯肯弗尔德教授则认为,对各种解释规则的适用“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理由是其“出发点、目标、论证方式及其程序”等都仍然还处于激烈争论之中。[30]现实状况也正如学者所言,联邦宪法法院在不同个案中对于解释规则的选择和运用似乎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即便对于同类案件而言,联邦宪法法院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解释规则。这一状况至少表明,学界对于释宪者在选择适用解释规则上具有“任意性”的指责是有一定依据的。问题是,解释方法上的任意性“必然会有损于联邦宪法法院的权威性”。[31]如果不能对各种解释规则的选择及其适用优先顺序形成共识的话,则宪法解释的正当性和可预测性无从得到保障,解释结论的说服力也自然无从谈起。
对此,吴庚先生的看法是:“像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那样,会在判决的理由中说明其引用的解释规则,肯定是‘有备而来’,并非得到结果之后,选择一种解释规则来自圆其说。……各种论点中如涉及法律的解释时,鲜有不是运用解释规则的结果。又如后述的合宪性解释,更是运用解释规则的结论,它的操作手段是用不同的解释规则,呈现多种结论,其中有合宪者,优先采用。如果都没有一种结论是合宪的,则在合理的限度内以转换文本意义的方式,认为系争的法律与宪法尚属相符。合宪性解释可谓真正的以方法寻求结论。”[32]
吴庚先生肯定了解释规则在形成解释结论过程中的实质意义,但是却仍然未能阐明法官究竟是如何运用各种解释规则得出结论的,其推论过程也颇值得怀疑。对于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引用”解释规则的做法,吴庚先生认为其“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一点当然毋庸置疑,因为联邦宪法法院应当不会毫无依据地“在判决的理由中说明其引用的解释规则”。然而“引用”是否即表明法院“并非得到结果之后,选择一种解释规则来自圆其说”,却还有待商榷,此问题且留待下文作出具体回答。而吴庚先生随后作出的“鲜有不是运用解释规则的结果”之判断,则多半是出于个人的揣测。此论尽管符合学界多年来致力于以解释规则学说限制释宪者主观任意性的学术努力之旨趣,但“鲜有”之说却并无依据,因为联邦宪法法院在裁判中明示其所适用的解释规则的情况毕竟比较少见。至于吴庚先生对于合宪性解释的论述,则更经不起推敲。如依吴庚先生所言,法官在作出解释之前似乎需要先行将各种可能的解释结论罗列出来,这在解释规则本身并未形成固定模式、而作为解释对象的宪法规范又通常具有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实际上并无实现之可能。此外,与其他解释规则一样,合宪性解释在解释结论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实质意义也还并不明确。由于合宪性解释首先必须取得的是一个“合宪性”结论,因此其不仅未见得如论者所言是“真正的以方法寻求结论”,相反却仍然还是“在个案中由法官自由决定解释规则是否有益于论证其所追求的解释结论”[33]。
吴庚先生所持的是规范逻辑的法实证主义观点,充分体现了传统概念法学中认为法律体系本身即具有自足性、完美性的思想,同时亦相合于纯粹法学所探求的“纯粹的”法律之应然这一逻辑结构意义上的价值追求。德国学界中与吴庚先生观点相似的学者不乏其人,例如近期还有学者提出:“法之内容,亦即解释之结果,取决于解释方法之选择。”[34]规范逻辑的实证主义学说的主要代表米勒教授认为,法学之理性体现在方法规则的适用上,因此“应规范化地评价各种解释规则的重要性”并“依据客观标准予以排序”。[35]为此他设计了非常复杂的解释规则评价与排序体系,并且为各种排序体系的选择适用方式又总结出了一套优先规则。但是,对于个案中具体应如何依据优先规则选择排序体系、应选择哪些解释规则、以及应如何确定各种解释规则之间的适用界限及其重要性顺序等问题,米勒教授也无法做出清楚的回答。他仅是笼统指出,实践中不应将他所提出的评价与排序体系及其优先规则当做解释规则,而应“批判性地适用该规则并根据经验予以改善”。[36]
对于米勒教授的观点,多数学者都持不同意见。克里勒教授认为,米勒之所以无法适用其所设计的规则,根源在于其所追求的独立于实体理由的解释规则并不存在,而恰恰相反的是,解释规则的发展与精细化必须以实体法上的案件事实为导向。[37]这就是所谓的“(解释)对象决定(解释)方法(der Gegen-stand bestimmt die Methode)”[38]。不仅如此,克里勒还进一步认为,米勒错在承袭了德国法学中长期存在的理论与实践之间脱节的传统,即“方法学说并非基于实践而形成(praxisorientiert),而是基于理论(教义)形成的(dogmatikorientiert),而理论(教义)则自视相对于实践而言是独立的”。[39]由于纯粹形成于理论之中的规则体系非但不能解决实践问题,反而因理论之不能自圆其说而引发了更多的理论问题,因此施林克教授也认为,米勒的法学方法论所引发的问题远多于其所能够解决的问题。[40]而早在1957年,本达教授就提出:“为各种解释规则确定一种层级式优位顺序的尝试是不可能实现的”。[41]施莱希教授则表示,“形成一种唯一的和统一的宪法解释方法是没有希望的”。[42]他认为,不仅不可能期望实现解释规则的法律化,而且也无法期望宪法解释能够完全遵守程式化的规则适用模式来进行。施林克教授也对此持相同的看法,并且认为:“如果各种推导步骤和解释标准的重要性及其优位顺序都无法确定的话,任何致力于实现单个推导步骤和解释标准的理性化和技术化的努力都是枉然的”[43]。而森德勒教授则指出,“如果缺乏了精神实体的话,所有方法上的认识都毫无价值。”[44]
不过尽管如此,联邦宪法法院对于解释规则的运用还是有其基本规律可循。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宪法解释不能仅依据某一种规则,而是需要综合运用包括解释要素和解释原则在内的各种解释规则,这就是所谓的规则综合模式(Methodensynkratismus)。[45]换言之,联邦宪法法院在个案中应基于具体情况,综合运用各种解释规则。至于究竟应如何“综合运用”的问题,则尽管还没有形成一种固定模式,但还是可以总结出一种“基本模式”:首先应以文义解释确定立法者的客观化了的立法意图,并以此确定解释结论的框架性内容。在此范围内,法官应适用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作为补充,来进一步精确定位基于文义解释所形成的结论。在必要的情况下,再以历史解释来印证该阶段性结论并作出必要的修正。此后再以宪法统一性原则、实际协调原则、功能正确性原则、整合效力原则、宪法的规范性效力原则等为标准来确定宪法规范所表述的精确含义。最后,再复核该解释结论是否满足合宪解释原则的要求。[46]
当然,此“基本模式”并不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而仅具有象征性的参考价值。毕竟个案中具体应当适用哪些解释规则、各种规则之间的相互关系究竟如何确定的问题,仍应取决于个案中的具体情况。正如一位曾任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的学者所言:“在我们这里,每个案件都有它自己的方法”[47]。勒莱克也认为,法院应根据其需要和必要性来运用解释规则,只要人们能够理解并且法院能够维持其权威性,那么解释规则适用中的“无原则性”基本上是无可指责的。[48]而克里勒则认为所谓的“规则综合模式”不过是“法官行使其自由裁量权的工具”而已。[49]因此即便上述“基本模式”可以成立,联邦宪法法院也未见得可以“按图索骥”式地作出裁判。质言之,联邦宪法法院对于解释规则的选取和适用并无确定模式。
实际上,对于解释规则在形成解释结论中的作用,多数学者都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森德勒教授明确指出,正是对于基本权利和宪法基本原则等特别重要的规范而言,文义解释、历史解释和体系解释等基本要素在许多方面都难以提供支撑。他甚至质疑解释规则起到的作用究竟是对于“裁判结果的合理化”还是对于“结论的伪装”,同时也认为学界总结的解释规则理论对于法官而言“既没有帮助也没有形成限制”。[50]姜爱生教授也同样对公认的解释规则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对宪法法院的裁判起到决定作用持怀疑态度。[51]从一定程度上而言,这些质疑的核心同时也指向了解释规则本身的“软肋”,即各种解释规则本身是否具有确定性的问题。例如文义解释所基于的“文义”本身常常就是不明的。历史解释所基于的是过去某个时期所形成的法律观点,其是否具有现实的合宪性仍有待审查。与此同时,由于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封闭的法律体系,并且大量现行规范并非为法律体系化之后的产物,而是在现有法律体系生成过程之中逐渐成形的,因此体系解释能否成立也颇值得怀疑。目的解释则更具有不确定性,因为规范本身是否包涵一个一以贯之的明确目的在内,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而即便规范本身有其“目的”,解释者往往也会难以在“规范的字面目的”、“规范制定者制定规范时所确定的目的”和“解释者认为规范应具有的目的”之间作出权衡取舍。也正因如此,学界普遍认为目的解释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一种任意解释(willkuerliche Auslegung)。[52]甚至于对以探求“规范中的客观化了的立法意图”为核心目的的客观解释理论,由于其所适用的解释规则并不具有明确性,有学者斥之为是“臆想的”[53]。至于应如何确定各种解释规则之间的适用顺序问题,则除了一个完全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本模式”之外,学界至今并未形成任何共识。对此,埃姆克教授认为,解释规则及其综合模式所能提供的仅是解决法学问题的一般性视角,而不能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法。[54]而哈弗卡特则反复强调解释规则与正确的法律发现(Rechtsfindung)之间毫无相关性,认为“遵守(解释)规则上的指示,既不是形成正确的法律发现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55]这些因素累积起来,得出的结论势必为:由于解释规则及其优先适用顺序不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所谓的规则综合模式所能给出的不过是一个仅具象征意义的基本模式而已。质言之,解释规则在解释结论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
四、宪法解释之结果取向
既然解释规则及其综合模式是“不明确”的,但却又不能是“任意性”的,那么在“不明确”与“任意性”之间,联邦宪法法院所应掌握的尺度何在?由于解释规则的选取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解释结论的形成,而法院又可以自主决定解释规则的选择和运用,因此如果不能够在此形成如何适用各种解释规则的“操作规程”的话,是否意味着法院完全可以自行决定解释结论?或许此推论本来就不具有被证成的可能性,因为即便撇开各种解释规则所具有的缺陷和不确定性不谈,欲使这一推论得以成立,尚须具备“解释结论完全系法院运用解释规则推论得出”和“依据解释规则推论出来的都是恰当的解释结论”两大基本前提。而这两个前提所指向的是同一个核心问题:宪法解释究竟是一种纯粹司法技术意义上的适法过程,还是其中融入了其他因素?换言之,究竟是应完全通过解释规则的适用来推知解释结论,还是解释结论实际上取决于解释规则之外的其他因素?
实际上,仅从解释规则及其综合模式不具有明确性这一阶段性结论中,就已经可以反向推论出宪法解释并非完全取决于解释规则适用的结论。与此同时,解释结论的得出也并非仅是一个法学方法意义上的技术性或逻辑性问题。相对于一般法律规范而言,宪法规范具有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其不过是一个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所形成的“框架性秩序”而已,因此仅从其条文本身也未见得就能够推论出个案中所需要的具体结论。对此,联邦宪法法院已经在其裁判中反复作出了说明。[56]虽然联邦宪法法院作为法院的职能在于依法裁判(即法适用),而似乎不应同政府或议会一样,在作出决定之前首先应主要考虑裁判结果的恰当性问题。但是,对于法官究竟是应当适用解释规则来获得解释结论、还是应基于解释结论来选择解释规则的问题,实践中出现的情况印证了后一种可能性:往往不是先要确定解释规则,而是先要形成解释结论,然后才能确定具体应如何适用解释规则,这就是所谓的宪法解释中的结果取向(Folgenorientierung),亦称结果考量、政治后果考察、政治后果取向、结果评判论证、价值判断、价值考量等。如果套用我国学界一度热议的“价值如何进入规范”之表述的话,则此过程就是一个“价值”透过结果取向“进入”并决定“规范”解释的过程。
有学者考证,所谓的“结果评判论证”实际上“最经常地出现在高等法院的判决中”。[57]其虽然从形式上而言似不应归属于解释规则的适用,但实质上却是解释者获取解释结论的重要方法,因此黑贝勒称之为“结果取向解释(Folgenorientierte Interpretation)”[58]。对此持相同看法的学者不在少数,例如哈弗卡特认为,必须以实体内容上的标准(inhaltliche Kriterien)来取代形式意义上的方法(formale Methoden),而结果取向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理性化标准(Rationalitaetskriterium)”。同时还应当看到的是,持规范逻辑的法实证主义观点的学者之所以强调解释规则的作用,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司法技术的完善来尽可能地排除政治因素对于宪法解释的影响,进而实现司法公正,但他们却并未完全否定结果取向在宪法解释中的作用,拉伦茨、卢曼、米勒等学者皆是如此。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将解释规则及其综合模式称为“形式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方法”,而将结果取向认定为“实质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方法”。
实际上,不仅是重大棘手的案件如此,即便是具体而微的争议通常也需要基于结果取向来获得具体解释结论,仅以著名的“有限数量判决(Numerus-clausus-Urteil)”为例说明如下:[60]
因有学生未能申请到大学医学专业的人学许可而诉至行政法院,行政法院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了法律解释请求,要求审查依据州大学法第17条对该专业的学生数量作出的绝对限定(absoluter numerusclausus)是否符合基本法。联邦宪法法院认为,鉴于超过半数的申请者不能获得入学许可,因此绝对的数量限制已经触及了宪法所能容忍的边缘。根据基本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的“自由选择学习地点的权利”、第3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平等原则以及社会福利国家原则,法院认为仅有在符合“已用尽现有学生容量”、“选择学生的标准符合实际情况”、“保障申请者机会平等并尽可能考虑个人对学习地点的选择”等要求的情况下,州法才能对于学生容量作出“有限数量限制”。而州法却未对选择标准的种类及其相互关系作出具体规定,因此该法为违宪的和自始无效的。
但是,如果简单宣布该法违宪的话,势必会使得大学“拥有了自行确定录取条件的紧急权能,而不再受到任何法律约束”,进而形成“离合宪秩序更为遥远”的混乱状态。从学校方面而言,其学生容量必然是有限的,尤其是对教学条件有较高要求的医学专业更是如此。因此,特定情况下只能要求学校应尽其所能地提供学习位置,而不能对之提出过高要求,以维护学校的正常运转和应有的教学质量。同时法院认为,学生是否拥有要求学校提供学习位置的权利、是否应满足所有学生的求学意愿等问题属于立法者的形成性自由权(Gestaltungsfreiheit)范围,而不应由法院在裁判中作出回答。综合上述考虑,法院认为,州立法者应于1973年夏季学期开始之前制定新的规范,而在此之前,学校应当继续遵守旧法的规定——尽管旧法已经被认定为是违宪的。
该案中,由于基本法第12条第1款和第3条第1款过于抽象,法官无法从中推论出具体结论,但又不能拒绝裁判(Rechtsverweigerungsverbot),因此只有通过寻找宪法框架中所可能容许的最佳处理方式作为裁判结果。在判决主文中,联邦宪法法院并没有就解释规则的运用作出阐释,而是直接依据对“超过半数的申请者不能获得入学许可是否符合宪法精神”的否定回答确定了法院的介入,进而通过对“州法是否应对该专业的学生数量作绝对限制”、“是否已经用尽现有学生容量”、“如果立即废止违宪的旧法会否出现更为不利局面”等诸多结果可能性的综合权衡,形成了法院的解释结论。
诸如此类直接依据对结果可能性的权衡来确定解释结论的判例,在联邦宪法法院判例集中可谓比比皆是。而对于结果取向在裁判结果形成过程中的具体功能,学界至少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观点认为,解释结论形成于法官对结果取向的认知,而解释规则仅是论证解释结论的工具而已。为证明此解读方式的正确性,森德勒教授曾以耶林的一段自述为证:“当需要为一个案件撰写专家鉴定或者给出意见时,他凭直觉就会迅速得出结论,然后紧接着拿起雪茄,思考应如何论证他的结论。”[61]而拉德布鲁赫则认为:“解释是一种结果。通常是在结果早已确定之后,才选择解释的方法。所谓的解释方法只不过是对文本的补充的事后的注脚而已。”[62]另一种观点认为,解释规则和结果取向共同作用于解释结论的形成,相对于解释规则而言,结果取向起到的是修正作用。例如洛舍尔德和罗特认为:“法律适用的方法首先形成于(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即形成于法官相对于立法者的地位,因此其在每一次法律适用中都是一样的。与此相反的是,实体法上需要考虑的法律地位则取决于具体的相关人和有争议的法律关系,因此所有由此而形成的修正并不必然具有普遍性”。[63]而格林则明确提出“裁判结果构成法律理由”的观点,并将结果取向认定为目的解释的考量因素之一。[64]苏永钦教授对结果取向的看法也大体同于第二种解读,他认为:“所谓结果取向的解释方法,简单说,即解释者把因其解释所作决定的社会影响列入解释的一项考量,在有数种解释可能性时,选择其社会影响较为有利者。”[65]
对于结果取向在形成解释结论过程中的实质作用,上述两种解读方式作了不尽相同的评价,其共同之处在于承认了结果取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是,何为此处所应予“取向”或“考量”的“结果”,却并不明确。通说认为,其取决于“利益权衡”、“价值”等实体法上的多种相关因素。由于“政治”一词可以涵盖极为广泛的领域,例如至少可以包括国家事务、权力的获取、对有关公益的决定施加的影响、敌我纷争、国家的自我维护、国家的领导、国家机关不受法律约束的意志力与形成力等[66],因此也可以将宪法解释中所需要考虑的各种因素统称为政治后果取向。但宪法解释中并非需要对所有可能的相关因素都作出考量,而是以与裁判所依据的规范的实体内容有直接关联者为限。[67]由于宪法规范的“开放性”及其所留下的较大解释空间,释宪者作出宪法解释时“不得不必须作政治衡量”,乃至于“即便是号称要求政治中立的宪法实证主义学派,其解释具高度抽象与概括性的宪法概念,单靠形式逻辑操作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毋宁大部份情形也都要借诸政治价值判断,所以倘一味坚持宪法解释的政治中立性,则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们有意或无意披着逻辑的外衣作价值走私。”[68]
不过,从联邦宪法法院作为法院的地位而言,其应当自觉履行法院的自我限制原则,即法院应尽量尊重其他国家机关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政治权衡和决定,以“使宪法规定由其他宪法机构自由作出政治决定的空间得以保留”[69],从而维护功能法观念主导下的国家机构之间的角色分配[70]。实际上,这一点已经在上文的“有限数量判决”中得到了充分反映。联邦宪法法院在该判决中明确表示,对属于立法者的形成性自由权范围内的事项,法院不宜代替立法者作出决定。从联邦宪法法院多年来的裁判中可以看出,所谓法律之外的纯粹政治上的考量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主要无外乎于“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宪法机关功能的维护”、“法的安定性”等成文宪法规范或不成文的宪法原则。由于宪法规范中已经将诸多一般性宪法原则包含在内,因此结果取向也可被视为是实现这些原则的基本方式之一。尤其是由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并不像美国最高法院那样拒绝裁判政治性问题,因此其是否履行法院的自我限制原则仅取决于其是否“自愿”。而实际上对于联邦宪法法院而言,作出政治性决定只不过是日常性工作而已,因为“在联邦德国的发展历程中,任何政治上有争议的领域都有联邦宪法法院参与其中”[71],以至于“政出卡斯鲁尔(联邦宪法法院所在地)”成为了对该法院的“一个古老的、流传广泛的和严厉的指责”[72]。
相对于解释规则及其综合模式而言,结果取向并非传统的解释与推论模式(das traditionelle Ausle-gungs-und Subsumtionsschema)中的组成部分。对此,卢曼依据其法律系统理论作出的解释是,“结果取向”不属于法律适用者的程式。[73]卢曼的观点也得到了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的支持,后者甚至在对法律论证与普遍实践论证作出区分的基础上,为解决应如何“在现行有效法秩序的框架内符合理性地作出决定”的问题,总结出了普遍实践论证“可能是有必要”的五种情况。[74]如果说传统的解释与推论模式可以对应于卢曼所称的法律适用和阿列克西所谓的法律论证的话,则学界形成的共识是将“结果取向”视为不同于解释与推论方法的过程。但由于联邦宪法法院从未在裁判中明确指明“结果取向”是形成解释结论的基础,而与此同时却在部分裁判中提及了其适用解释规则的过程,因此容易形成法院的解释结论得之于解释规则上的推论而非形成于结果取向的错觉。
当然,联邦宪法法院基于结果取向所确定的解释结论未必就是完全正确的。对此,1970年所增加的联邦宪法法院法第30条第2款第1句规定,每位法官都可将其在案件评议中对裁判或仅仅对裁判理由提出的“不同观点”记录为一个特别意见(Sondervotum),并将之与裁判正文一道公开。虽然引入特别意见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法律政策意义上的法律观点储备功能,而与宪法解释方法并无直接联系,但是该制度的存在至少表明了个案中作出不同宪法解释的普遍可能性。而且彼时屈居“特别意见”的观点,日后却能转变为主导性意见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虽不能谓之比比皆是,却也屡见不鲜。因此有学者指出:“特别意见这一制度的引入,是宪法问题中在宪法解释方法和结果上的多元性的表现。”[75]
不过即便有此“多元性”的存在,解释结论不能超出于宪法解释应有的界限之外,应是毋庸置疑的。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对这些所谓的“界限”的遵守也是法院所应“取向”的“结果”之一,其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宪法解释必须以宪法文本为基础。基本法第1条第3款和第20条第3款明确规定了宪法的优先(Vorrang der Verfassung)。联邦宪法法院不能凌驾于宪法文本之上,因为文本是法院作出裁判的基本标准和根本依据。为此,联邦宪法法院明确将宪法文本的字面表述称为“宪法解释的不可逾越的界限”。[76]当然,宪法解释者所探求的乃是文本中所表明的立法者的“客观意图”,因而又不必完全以宪法文本的字面表述为限。在“为法律的有意义的适用而有所必要”或者“更能符合宪法的价值取向”的特殊情况下,宪法解释也可以突破宪法的字面表述。[77]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任何宪法规范作出的解释,都必须要符合立法者所确定的基本宪法原则和基本决定”。[78]概言之,宪法解释原则上必须基于宪法文本,并以宪法文本所表达出来的立法者的客观意图为限。
其次,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解释权会受到立法权和行政权的限制。宪法的优先不仅适用于联邦宪法法院,同时也适用于立法机关。联邦宪法法院对立法机关依民主程序所制定的规范进行审查和作出解释,本身就对立法机关的权限构成了限制。[79]对此,如果用法官博肯菲尔德在一个颇为著名的判例中所发表的意见来表述的话,就是宪法解释会“改变由基本法所确定的立法机关和宪法法院之间的分权关系”。[80]在法治国家中,立法权应当由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立法机关来行使,联邦宪法法院裁判的效力不应高于议会的决定。换言之,应尊重议会在立法上的优先权,而不应挑战立法者在政治上的形成性自由权。因此,为维护基本法中所确定的权力平衡,联邦宪法法院必须保持其在司法上的自我克制,以尽量不触及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规范的权力并认同现行法中所确定的法律状况。[81]而与此同时,由于宪法规范—尤其是基本权利规范—对于立法权起到了确定和限制的作用,宪法解释同时也起到了厘定立法权范围的作用。[82]立法机关如欲对抗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解释,唯有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改变宪法的法律(verfassungsaenderndes Gesetz)”这一途径(基本法第79条)。[83]因此,“保护宪法和形成宪法是立法者和联邦宪法法院的共同任务”。[84]与此同时,联邦宪法法院也不能触及政府的形成性裁量范围,尽管“这些界限至今仍未被作出明确界定,并且有可能它们本来就是无法界定的。”[85]
再次,宪法解释会受到法官造法的限制。正如毛雷尔教授所言:“宪法规范经解释和适用而在某个方向上增加了其意义内涵(Bedeutungsgehalt),将来(的解释或适用)不可简单无视其存在。”[86]而随着司法裁判的逐渐积累,法官造法的可能空间也会被大量裁判所堆积和填充,从而缩减法官的判断余地——在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中随处可见的对判例的梳理、分析与鉴别即是如此。具体而言,原有案情相同或者相近的判例往往会对裁判方向形成直接影响,而案情相异的判例则可以起到重要的证伪作用。此外还有另一种形成于司法审级关系(Instanzenzug)之中的限制,即上级法院的裁判会对下级法院形成事实上的判例效力(praejudizierende Wirkung)——即便并无成文规范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最后,宪法解释要以能够得到广泛的接受为限。联邦宪法法院的解释虽系针对个案作出,但由于其具有普遍性的拘束力,因此解释结论应当是具有“普适性的(verallgemeinerbar)”。“这对于宪法解释而言构成了界限,同时也保证了裁判的可预测性”。[87]为此,在确定解释结论之前,法官必然要参酌其他国家机关对该案所可能会形成的看法,以及社会公众可能会有的后续反应。
五、在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之间
可以设想的是,法官在确定个案中的结果取向之时,必然要对形式意义上的规则综合模式之容许性有所考虑——即便其未见得需要在裁判中明示所适用的解释规则;而在筹划个案中具体适用的规则综合模式之际,法官也不能不以结果取向之论证需求为导向——尽管其通常不会明示具体的结果取向考量过程。[88]因此本文认为,宪法解释方法不应仅指传统的解释与推论模式中的解释技术,而是应同时将结果取向涵盖在内,这也是上文把解释要素和解释原则统称为“解释规则”而不是“解释方法”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对于规则综模式与结果取向在形成解释结论过程中的作用,学界早已在不同的论证层面作出了阐述。例如拉德布鲁赫认为:“法学解释是理论和实践、认识性和创造性、创作和再创作、科学性和超科学性、客观和主观各种因素不可分割的混合。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践的、创造性的、创作的、超科学性的,是由不断变化的法律需要所决定的。因此,作为法学解释的目的和结果的立法者意志也不会由对确定内容的解释永久地固定下来,而是要一直保持解答具有新含义的、变化了的时代关系所提出的新的法律需要和法律问题的能力。我们不能把立法者的意志理解为某一次引起法律产生的意志事件,而是应该把它理解为不断变化的、承担法律(制定)的成就意志。”[89]哈贝马斯则提出了所谓的“司法的合理性问题”:“一种偶然地产生的法律的运作,如何才能既具有内部自洽性又具有合理的外在论证,从而同时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的正确性呢?”[90]
但是,上引两位学者却并未具体说明,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分别在形成解释结论的过程中具体承担了哪些功能。为回应此问题,一些学者致力于从自康德以来即得以确立的法律发现(Findung)与法律论证(Rechtfertigung)之间的区分入手解决问题。例如黑贝勒教授认为,一般性的宪法规范系生成于其时未见得为人所尽知、且不能构成一个封闭体系的现实基础上,因而从规范中未见得能够推论出适用于个案的解释结论,而是必须凭借一定程度的非基于法学方法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够发现结论(法律发现阶段)。为此,他甚至还提出了“宪法解释的民主化”问题,认为宪法解释者本身应可以组成一个“开放的社会”,故而应弱化其司法因素而强化其他主体的参与作用。[91]因此,对于规范的适用是否恰当的问题,不能依据证实标准(Kriterium der Verifikation)来作出评价,而只能依据证伪标准(Kriterium derFalsifikation)来判断(法律论证阶段)。质言之,对于并非处于封闭体系状态之下的客观现实而言,一般性规范的适用结果可以通过法学方法得以论证,但是其发现过程必须包含有非法学方法因素在内。[92]而在施林克看来,黑贝勒仍然没有解决解释规则与结果取向之间关系为何的问题,因为“获取解释结论阶段中起作用的前理解、偏见、个人倾向和政治价值判断与在论证结论阶段中起作用的解释规则之间毫无关系”。[93]不过施林克也不得不随后承认:“尽管联邦宪法法院原则上承认采用了传统(解释和推论)模式,但是其实际上是以实体上的论证为基础的,并且法院也未能阐明实体论证与传统模式之间的关系”。[94]对此,米勒给出的解释是:司法裁判不同于其他科学发现之处恰恰在于,司法裁判所需要展示的不是其发现过程,而是其论证过程,即法院需要通过对论证过程的展示来实现法治国家原则中所提出的理性化和可控性要求。[95]
舒尔泽一菲利茨则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结果取向对于形成解释结论的意义。他对于近年来颇受争议的一些著名案件作出综合分析之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在他看来,尽管联邦宪法法院对于所有案件给出的裁判都具备法学上的理由,但问题是那些被联邦宪法法院所抛弃的观点同样具备法学上的理由。[96]并且,即使是由联邦宪法法院基于合议庭的“意见一致”而作出的裁判,其解释结论“几乎从来都不可能(fast nie)”是唯一正确的结论。[97]那么,法院应如何在数个不同的正确结论之间作出取舍呢?这在作为司法技术的解释规则层面而言,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诸多解释规则及其综合模式的背后,究竟隐含了解释者的何种思辨过程,似乎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论证。不过,舒尔泽一菲利茨的发现至少证明了,宪法规范在特定情境之下提供的正确答案并不具有唯一性。换言之,通过演绎方法得出的答案通常并不是唯一的。
克里勒认为,应在传统的解释方法学说和新的解释方法学说之间作出区分。传统的解释方法学说以从法律中“正确地推论出结论”为核心,认为解释方法的作用不过是“发现(立法者)已经作出的决定”而已,因此应由立法者而不是解释者来对该决定负责。而依据新的解释方法学说,法律人在适法过程中不仅应进行“推论”,而且同时也参与了规范的形成,其作出的是一个“负有责任的决定”。确切而言,法律人不仅应“忠于法律”地作出决定,而且同时负有作出不偏袒和公正决定的义务。在此基础上,克里勒进而认为,传统学说是基于法学理论(教义)而不是在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因而其属于“法学的方法论(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其强调的是法律发现(Rechtsfindung)的推论过程。而新的解释学说则以法律获取(Rechtsgewinnung)为核心,“诠释、方法、逻辑和具体化因素等”不过是“最低条件(Minimalbedingung)”而已。换言之,使实体法上的争议得到解决的并不是这些形式意义上的解释规则,而只能是事实内容上的论证。[98]克里勒的贡献在于强调了被传统解释方法学说所忽视的结果取向的价值,并赋予其在法律解释中的核心地位,这也是克里勒的观点区别于拉伦茨、卢曼、米勒等人之处。对于克里勒的观点,卢曼指出其缺陷在于“结果”之复杂性问题未能解决,因为“结果、附带结果、结果之结果多至无法估量,以至于只能够有所选择地对之作出预测和评价”,而克里勒却未能为如何进行“选择”提供一个标准。[99]拉伦茨则经克里勒批评之后,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后来也承认“解释者本身对解释结论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100]不过对于结果取向,拉伦茨还是部分地持保留意见,例如他认为民事法院就不必注重结果考量,而“宪法法院也未必能确实综观所有(遥远的)结果,虽然其可能性要大于民事法院”。[101]由此可见,反对或部分反对克里勒观点的理由主要集中于“结果”之不确定性,但都并未否定结果取向所具有的实质意义。
还有学者试图通过将结果取向导入目的解释、并以此达成两者之间对接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例如洛舍尔德和罗特提出,“结果取向”所考量的仍然是立法者所作出的实际价值判断,因此“如果不能确定立法者所作出的实际价值判断的话,就必须通过目的解释的方式来探求立法者可能的价值判断,并以此来确定规范的内容”[102]。与其他解释规则所不同的是,此处的目的解释并非旨在探求规范文本的含义或立法者的真实意图,即其并非建立在一个(被立法者)先定的认知目标的基础之上。对此,阿列克西也持基本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目的解释所探求的目的,“不是依据过去和现在实际存在着的任何个人的目的,而是依据‘符合理性的’或‘在现行有效的法秩序框架内客观上所要求的’目的”[103]。而联邦宪法法院也明确提出:“目的解释不仅仅是(可被事后验证的)认知行为,而绝对是包含有创造性因素在内的。”[104]如果说解释者应当以立法者的价值判断为基础的话,其在个案中所作出的判断应当比立法者更为具体和切合实际,即“不仅要重现立法者的价值判断,而且必须要自行构思出来一种价值判断”[105]。由于目的解释可以融汇立法者与适法者的价值判断于一身,而在解释方法的层面上又可以将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统摄其中,因此有学者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经典四方法”,“只有唯一的、包涵文义、历史和系统解释三要素在内的目的解释方法”。[106]而这样的目的解释的主导思想和首要目标又在于从所有可能的解释结论中“选择与立法者作出的其他决定最为协调的价值判断”,以“尊重(立法者)价值判断的内在协调性”。[107]因此,即便将结果取向和规则综合模式导入目的解释框架之中,所得出的仍然是以解释者应兼顾解释规则的适用和结果取向、并以结果取向为核心考量因素的结论。
也许正因为解释规则及其综合模式仅仅能够起到论证解释结论的作用,而真正对解释结论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结果取向,因此对联邦宪法法院法官的根本要求似乎并不在于法学知识与素养,而在于政治上的平衡。以至于在评议联邦宪法法院法草案之时,认为法官职位可以由非法律专业人士担任的观点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主要理由之一则是非法律专业人士应能“把政治的、基本法所确定的新政治秩序精神的特别意义,引入到法院的裁判之中”。[108]而对于法官的政治倾向问题,则以要求承担选任法官任务的议会机构的三分之二多数同意的方式予确保。因为获得如此特定多数而出任法官之人,通常也就是各派政治力量经反复权衡后可以共同认可的人选,其所作出的裁判也较能获得接受和信赖。而正是由于法官选任制度中的上述设置,法官的前理解(Vorverstaendnis)对于裁判结果的影响不仅未受到制度性限制,而相反却是得到制度支持甚至是强化的。对此,现任联邦宪法法院副院长哈塞默教授给出的证据是,在其任职第二审判庭法官十二年的时间内,该审判庭仅有两次作出了不同于该庭法官所属政党路线的裁判。[109]这不仅从现实角度表明了法官的前理解对于裁判结果可以起到事实上的决定作用,而且也再次证明了结果取向在形成解释结论中的决定作用。
质言之,面对宪法规范留下来的较大解释空间和受到政治影响的诸多可能性,宪法解释应当是一个融汇法适用与结果取向于一体的过程。既为法适用,则要求由掌握司法技术的法官来执掌宪法解释;而对于结果取向,又须以解释者具备合适的政治身份为核心。结果取向为解释结论的确定奠定了基础,而规则综合模式则提供了论证工具。对于解释规则,法院虽然只是偶尔会明示于裁判文书之中,但实际上即便是在并未明示解释规则的其他大量裁判中,解释规则依然作为论证工具存在。对于结果取向,虽然法院一般不在裁判文书中作出明确说明,但其在寻求解释结论的过程中却多以结果取向为基本导向。因此,宪法解释方法由形式意义上的规则综合模式与实质意义上的结果取向共同构成,两者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界限虽不甚分明、但却张弛有度的弹性妥协机制,使得宪法解释既能在实质结论上维护宪法原则和精神,又在形式意义上经得起解释规则及其综合模式的验证。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一游离于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之间、致力于获取解释结论正当性的权衡取舍过程,本来就形成于同一思维之中,解释者的前理解及其对于结果取向的权衡则贯穿于解释过程始终。因此,无论“机制”之设计何等精密、解释方法内含之诸要素如何周延,解释结论的得出从根本上而言仍然维系于解释主体在个案中形成的主观判断,故而解释规则及其综合模式终究无法取代法官的“前理解”而成就为宪法解释的客观准则,而“谁是最合适的法官”则始终是对宪法解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核心要素。
当然,在具体个案中,规则综合模式和结果取向所起到的作用也可以是不均衡的,甚至于法官还可以全然不顾两者所组合成的解释方法、而仅凭对现有判例作出的梳理就可以获得正确的结论。因此,即便本文探究宪法解释方法至此,也不得不认同黑塞所谓的“宪法解释结论的正确性……永远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得到精确证明”[110]之语,毕竟宪法解释“不是算术题,而是一种有创造性的精神活动”[111]。
六、面向中国的宪法解释方法
宪法解释在形式上应经得起解释规则及其综合模式的验证,但其实质意义上的正当性则取决于基于结果取向所获得的解释结论。在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之间,规则综合模式的确定需要以结果取向中所得出的解释结论为依托,而结果取向对于解释结论的决定作用也被限定在规则综合模式所可能容许的范围之内。作为宪法解释方法一体之两面,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应并行成为构建我国宪法解释方法的基本工具,而不可有所偏废。
从解释规则的层面而言,我国宪法解释制度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法定解释主体是否具备适用解释规则的能力。虽然我国宪法第67条规定的宪法解释主体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并非如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一样为司法机关。但从上文的考察中可以得知,解释规则在形成解释结论过程中的实质作用是难以确定的,仅有可能要求释宪者遵循规则综合模式这一基本规律,而无法期望其能够完全遵守程式化的解释规则适用模式。因此即便是司法性的宪法解释主体,也不能如同部分学者所期望的那样,完全基于传统的解释与推论模式来获得解释结论。就此而言,则问题的关键在于解释主体能否遵循解释规则的基本适用规律,而不在于其在组织性质上为司法机关抑或立法机关。因此,即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适用解释规则的能力会弱于司法机关,但其同样可以具备相应的能力应是无疑的。实际上即便是在德国,学界也并未因联邦宪法法院为司法机关而否认立法机关可以具备适用解释规则的能力,而宪法解释机构可由非法学者组成的观点不仅在联邦层面一度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在州的层面甚至至今仍占据主导地位。当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应将宪法解释完全混同于其他决定,而应尽可能明示其适用解释规则的论证过程,以使宪法解释论证有力而不是仅仅给出最终结论。实际上,正是由于解释规则的适用并无固定模式,因此在制度化的宪法解释机制在我国得以实现之前、乃至于在其经过相当长时间实际运作之后,完全有可能仍然无法形成固定的规则综合模式。甚至于如何确定各种解释规则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等更具基础性的问题,也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解决。因此我们不能期望先行从理论上彻底解决应如何适用解释规则的问题,然后再行启动宪法解释,而应把该问题留待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相信随着释宪实践的洗礼,中国式的规则综合模式也必然会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的持续冲撞中得以逐渐成型并日益切合实际需求。
就结果取向而言,则只能认为在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宏观态势的准确把握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明显优于司法机关。对于具有开放性和不确定性的宪法而言,宪法解释中第一位应当予以考虑的因素应是解释结论对社会政治生活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法官通常仅能着眼于个案中具体纠纷的解决,而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此外,尽管我国宪法序言最后一段中明确表示该法具有“法律的形式”,但是现行宪法还未能形成一个成熟的规范体系却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我们可以期望宪法解释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宪法文本中的漏洞,但是这样的弥补首先应建立在宪法本身为“规范宪法(normative Verfassung)”的基础上。否则,宪法解释必然要经常地和在相当大程度上在相互冲突的规范和价值取向之间作出选择,从而使宪法解释者在实际上承担立法者的角色,进而破坏两种角色之间应有的分工与平衡。因此,至少在我国宪法文本得以成就为一个规范性的统一整体之前,宪法还无法脱离其制定者,即不宜由人大以外的其他机关来对之作出解释。当然,即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宪法解释任务,其在宪法解释中所应权衡的“后果”究竟有哪些、应如何权衡各种“后果”等问题,仍有待于澄清。此外,人大常委会之下是否应专门设立具体承担宪法解释任务的机构、该机构人员如何组成、应如何设定宪法解释程序、究竟应限于“抽象解释”还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作出“具体解释”、如何定位宪法解释的先例效力等问题,也还需要作出进一步的研究,但这些已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之内。
综合考量宪法解释方法的上述两个面向,不难发现作为我国宪法所规定的解释主体,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在适用解释规则的能力上可能会弱于司法机关,但从结果取向而言则明显优于后者。由于实质意义上的结果取向决定了解释结论的实体正当性,而规则综合模式仅能够起到形式意义上的论证作用,因此仅就解释方法而言,现行宪法所预设的立法解释模式实质上更为符合中国现实所需。尤其是在预期现行宪法仍然会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现实条件之下,激活其所预设, 的立法解释模式并充分发挥其制度功能,倚重解释主体作出的结果取向之正当性来获取适当的解释结论,并尽可能对之作出解释规则层面上的论证,不失为推进当前, 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务实之选。如果能够真正激活宪法解释的话,那么在此形成一定程度的“方法论上的觉醒”[112]也是可以期待的。但由于“方法”之形成、检验及逐步完善皆取决于适用“方法”之实践,而理论上的“方法”之推演仅能起到总结归纳而非创制作用,因此即便在“觉醒”之后,要形成符合中国现实所需的宪法解释方法,尚需一个并不短暂乃至于相当漫长的实践过程,甚至于经过长期积累之后仍然还有可能无法形成具有明确可操作性的宪法解释方法模式。如此一页宪法解释实践史既然可以在德国上演,也完全有可能会在中国重现。质言之,就宪法解释方法而言,至为重要的是在释宪实践中逐步形成符合现实所需的方法模式,而不可期望在此之前先行在学理上获得解释理论的成熟与完善。
近年来,我国学界甚为关注的是司法性的宪法解释模式,而美式宪法解释体制及其理论则常被引以为学术蓝本。例如有学者认为,如果要使宪法典成为具有实效的最高法,最为关键的制度设计就是司法性的宪法解释制度。[113]为论证该结论,学者们总结了司法解释模式的种种功能。[114]但对于立法解释模式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具备相应功能的问题,学者们却或多或少采取了直接否定的态度。实际上,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实行的议会主导的宪法解释制度同样具有正当性,因此各国完全可以视具体情况采用立法性或司法性的宪法解释模式。而与此同时,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现实具体状况而言,更具有权威性的宪法解释者无疑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最高法院或一家宪法法院。司法性的宪法解释制度不仅不符合我国宪法体制,反而还有可能会使得法院被迫承受不可承担之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司法化论者的对与错都在于其历史意识的片面性,在于他们仅仅顺应了个体化和法制化趋势,缺乏对中国政治类型的正确和全面的判断。”[115]至于“我国人大常委会几乎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从未行使宪法解释权的事实”,的确揭示了该机关基于种种考虑而怠于作出宪法解释的现状,但却并非如学者所言是“反证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宜成为宪法解释的主体”。[116]恰恰相反的是,这表明了当前应当正视的是如何激活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的问题。当然,司法性的宪法解释模式所具有的优越性,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总结,而本文实际上也是在为此而做出努力。但在宪法解释方法问题上,考察司法性的宪法解释模式所适用的解释方法究竟为何并探讨其对于我国制度的实质意义,以及积极寻求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去解决现实问题,相比较于纵论宪法解释体制变革的建言来说,似乎更具有中国法意义上的现实性。
今日中国社会状态之多样化以及变迁频率之快,恐怕已非现行宪法文本的制定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之时所能设想。为应对现实所需,适时修改宪法文本往往成为必然之选,而以宪法解释解决现实问题的机制却仍然未能实际形成,从而形成了宪法解释与宪法修改脱节、重修改而轻解释的局面。实际上,即便我们可以完全无视宪法第67条第1项对于我国的宪法解释机制作出的明确规定,也不应对现实中日益增长的宪法解释需求熟视无睹。因此,当前真正所面临的问题应是如何在尽可能少付出制度变迁成本的前提下,激活现行宪法所预设的宪法解释制度,使得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宪法问题可以通过虽未得以完全固定、但毕竟具有相当程式化的解释技艺而得到解决。而在现行宪法解释制度中还有哪些可供开拓的制度空间尚未探明、且这一制度并未经过实践充分检验与修正的情况下,径言体制改变的问题,似乎还为时过早。在此套用一句苏力的话,那就是:“我支持制度的追求,但首先得解决具体问题”[117]。换言之,至少在用尽现行制度所提供的可能性之前,不应考虑改变制度的问题。因此,首先应当做的是“尊重已经建立起来的法律秩序与法律传统”并致力于“从已经确立的法律秩序中生长出新的规则”。[118]至于现行宪法得以制定之时,为何未对宪法解释制度所应适用的具体规则和程序作出任何规定的原因,现在已经难以作出准确的考证。甚至于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认为,立宪之时作如此安排的目的,正是间接表达了当时并不倾向于真正启动宪法解释制度的意愿。但无论如何,如果现在需要激活宪法解释制度的话,首先应尽可能对解释规则的适用和解释程序作出具体规定,这是启动宪法解释制度的基本前提。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规则的缺失使宪法解释即使可能也无法避免解释者的主观恣意,无规则的所谓解释只会令宪法的规范性与权威性受到解释者主观价值判断的侵害。所以,建立宪法解释的规则体系是我国开展宪法解释工作并使其客观化、科学化的当务之急。”[119]
然而臻于完美的宪法解释方法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在有着近六十年释宪实践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其所适用的宪法解释方法中也还有许多无法确定的内容。如果继续向下追问,则各种解释规则的内涵和外延及其“综合模式”依然不甚清楚、结果取向中具体应当考虑哪些结果以及这些结果之间的关系如何仍然无法确定、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在形成解释结论过程中的弹性妥协机制究竟应如何才能张弛有度也不甚明了。而如果向上溯源,则问题还可以回到演绎与归纳之间的基本逻辑区别,乃至于上溯至实证法与自然法之争。因此在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之间,联邦宪法法院究竟如何获得恰当的解释结论,似乎是一个永远无法得出最终结论的课题。然而在规则综合模式与结果取向两个面向及其所内涵的诸多因素相互交织作用之下,联邦宪法法院毕竟可以通过具有相当司法程式化的宪法解释方法模式得出其解释结论。因此尽管本文并未能够完全澄清宪法解释方法中的所有问题,甚或本文提出的问题还远比所解决的问题要多;但人类智识的发展或许原本即如此,已经获得的认识永远无法解决所有已经意识到的问题,而推动人类智识向前发展的正是致力于解决这些现存问题的持续努力。在此意义上,本文愿以克里勒教授的如下表述作为结语:
在需要为具体个案作出裁判时,不能期望首先要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都讨论清楚,而是必须要在某时作出“决定”。但人们却不是“非理性地”作出决定,而是基于一种诚然尚未终结的理性探讨来作出决定。因此在整个过程中,人们的智识得到了理智的法的续造的补充;这一反省不断继续进行下去,新的经验得到了吸收,人们有理由相信,错误的裁判会在将来得到纠正。[120]
【作者简介】
刘飞,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
[1]韩大元:《现代宪法解释学:基本框架与方法》,载韩大元等:《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2]关于此两种模式的区分,详见许宗力:《集中、抽象违宪审查的起源、发展与成功条件》,载许宗力:《法与国家权利(二)》,台湾元照出版社2007年版,第3-40页。
[3]前引[2],第3页。
[4]Hesse, Grundzue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0. Aufl. 1995, Rn. 49.(本书中文版参见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5]前引[4],第20页注[3]。
[6]Zusammenfassend Bleckmann, Zu den Methoden der Gesezesauslegung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VerfG, JuS 2002,942, 946.
[7]Badura, Staatsrecht, 3. Aufl. 2003,A 13.
[8]Kirchhof, Die Aufgahen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in Zeiten des Umbruchs, NJW 1996, 1497,1503.
[9]Starck, Verfassungsauslegung, in: Isensee/Kirchhof,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VII, S. 189, 193 ff.
[10]Isensee, Verfassungsrecht als “politisches Becht” , in: Isensee/Kirchhof,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and VII, S. 146.中文引自陈爱娥:《宪法作为政治之法与宪法解释—以德国宪法学方法论相关论述为检讨中心》,载《当代公法新论(上)—翁岳生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724页。
[11]联邦宪法法院法第31条第1款:“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对于联邦和各州的宪法机构以及所有的法院和行政机关而言都具有拘束力。”
[12]Vgl. etwa Katz, Staatsrecht, 16. Aufl. 2005,Rn. 109.
[13]BVerfGE 30, 157ff.
[14]BVerfGE 11,126, 130.
[15]Maurer, Staatsrecht I, 2. Aufl. 2001,§ 1 Rn. 49.
[16]BVerfGE 35,263,279.
[17]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n Roemischen Rechts, Bd. 1, Berlin 1984, S. 213.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解释要素的分类存在不同的看法,例如萨维尼所称的四要素中就包含有“逻辑(论理)解释”而并无“目的解释”,而其他学者提出的还有比较法解释(k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主观解释(genetische interpretation)等要素。本文限于目的和篇幅,不对此做出论述,而是直接采用联邦宪法法院裁判中所明确认可的四种基本解释要素。
[18]参见吴庚:《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第3版,第498页以下。
[19]详见前引[4],边码70以下;前引[15],第1章边码60以下。
[20]BVerfGE 19,206,220.
[21]BVerfGE 19,206,220; 30, 1,19;33,23,29; 39, 334, 368;55,274, 300.
[22]Boeckenfoerde, Die Methoden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Bestandaufnahme und Kritik, NJW 1976, 2089, 2097 f.
[23]So z. B. Sodan/Ziekow, Grundkurs Oeffentliches Becht, 2005,§2Rn.11; Starck,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in der Verfassungsordnung und im politischen Prozess, in: Badura/Dreier(Hrsg.),FS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2001,Band I, S. 1,19.
[24]Sachs, in: Sachs(Hrsg.),Grundgesetz, 3. Aufl,2002, Einf. Rn. 46.
[25]前引[9],第199页以下。Starck教授的上述观点亦见于李建良:《宪法理论与实践(一)》,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第2版,第200-204页。莱尔歇也明确指出宪法法院的解释方法“原则上并无特殊之处”,见Lerche, Stil und Methode der verfassungrechtlichen Entscheidungspraxis, in: Badura/Dreier(Hrsg.),FS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2001,Band Ⅰ, S. 333,335。
[26]Looschelders/Roth, Juristische Mothodik im Prozess der Rechtsanwendung: zugleich ein Beitrag zu den verfasungsrechtlichen Grundlagen von Gesetzesauslegung und Rechtsfortbildung, 1996, 5.204.
[27]Vgl. Engisch, Einfuehrung in das juristische Denken, 8. Aufl. 1983,S. 82 ff.
[28]Kaufmann, Problemgeschichte der Rechtsphilosophie, in: Kaufmann/Hassemer(Hrsg.),Einfuehrung in Rechtsphilosophie und Rechtstheo-rie der Gegenwart, 6. Aufl. 1994,S. 30, 165.
[29]Mahrenholz, Verfassungsinterpretaion aus praktischer Sicht, in: Schneider/Steinberg(Hrsg.),Verfassungsrecht zwischen Wissenschaft und Richterkunst, Kolloquium aus Anlass des 70. Geburtstags von K. Hesse, 1990, S. 53,60.
[30]前引[22], Boeckenfoerde书,第2089页。
[31]前引[25], Lerche书,第335页。
[32]前引[18],第555-556页。
[33]Kriele, Theorie der Rchtsgewinnung, 1976,S. 25.
[34]Jestaedt, Wie das Becht, so die Auslegung. Die Rolle der Rechtstheorie bei der Suche nach der juristischen Auslegungslehre, ZoeR 2000,133,135.
[35]Mueller, Juristische Methodik, 2. Aufl. 1976, zitiert aus Kriele, Theorie der Rchtsgewinnung, 1976,S. 317.
[36]前引[35],第318页。
[37]前引[33],第318页。
[38]Zippelius, Junstische Methodenlehre, 8. Aufl. 2003,Einleitungssatz, S. 1.
[39]前引[33],第319页。
[40]Schbnk, Bemerkungen zum Stand der Methodendiskussion in der Verfassungsrechtswissenschaft, Der Staat 1980, S. 73,99.
[41]Bender, Zur Methode der Rechtsfindung bei der Auslegung and Fortbildung gerechten Rechts, JZ 1957,593 ff.
[42]Schlaich, in: VVDStRL 39, 1980, S. 208.施莱希教授的上述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很多学者都对此做出了相近的表述。例如里德尔认为,每一个案件所需要的都是仅适合于该案的独特的解释方法,不应公式化地运用各种解释方法,而必须使解释方法的运用要适应于个案的具体情况。参见Riedel, Methoden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 im Wandel, in: FS Schneider, 1990, S. 401.
[43]前引[40],第78页。
[44]Sendler, Die Methoden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Rationahsierung der Entscheidungsfindung oder Camouflage der Dezision? FS Kriele,1997, S. 482.
[45]BVerfGE 11,130.
[46]此基本模式形成于对主流学者观点的综合。中文资料可以参见[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9页以下;黄茂荣:《法律解释》,载《法律哲理与制度—基础法学:马汉宝教授八秩华诞祝寿文集》,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381页以下。有学者提出所谓的解释规则层级说,其实质内容也与此基本相同,参见前引[26],第193页。
[47]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页。
[48]Roellecke,Prinzipien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 in der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in: Starck(Hrsg.),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Grundgesetz. Festgabe aus Anlass des 25jaehrigen Bestehens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Zweiter Band, S. 22,48.
[49]前引[33],第26页。
[50]前引[44],第465页。
[51]Ebsen, Der Beitra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zum politischen Grundkonsens, in: Schuppert/Bumke(Hrsg.),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gesellschaftlicher Grundkonsens, 2000,S. 61, 89.
[52]Vgl. zusammenfassend Wolff/Bachof/Stober/Kluth, Verwaltungsrecht I, 12. Aufl. 2007,§28 Rn.45.
[53]前引[47],第340页。
[54]Ehmke, Prinzipien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 in: VVDStRL 20(1963),S. 53,59.
[55]Haverkate, Gewissheitsverluste im juristischen Denken. Zur politischen Funktion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 1977, S. 18.
[56]例如在涉及信仰保护的裁判中,联邦宪法法院的经典表述为:“基本法并未着意于保护任何一种信仰,也不保护任何一种类似于信仰的活动,其所保护的只有现今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基于特定一致的基本道德观念所形成的信仰。”因此,基本法条文中并未明确规定其保护的是何种信仰。换言之,仅从基本法条文之中,无法推论出其所保护的信仰为何的具体结论。参见BVerf-GE 12, 1,4。
[57]施罗特:《哲学诠释学与法律诠释学》,载考夫曼、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注55。
[58]Haeberle, Zeit and Verfassung, in: Dreier/Schwegmann(Hrsg.),Probleme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 Dokumentation einer Kontroverse.Baden-Baden 1976, S. 305 ff.,309 ff.
[59]前引[55],第207页。
[60]下文对该裁判的评述及总结系根据载于官方判例集的裁判文书整理而成,该判例具体内容详见BVerfGE 33,303。
[61]前引[44],第465页。
[62]Radbruch, Einfuehung in die Rechtswissenschaft, 12 Aufl. 1969 S. 169.转引自前引[47]。
[63]前引[26],第15页。
[64]Grimm, Entscheidungsfolgen als Rechtsgruende: Zur Argumentationspraxis des deutschen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in: Teubner(Hrsg.),Entscheidungsfolgen als Rechtsgruende, 1995,S. 139 ff.
[65]苏永钦:《结果取向的宪法解释》,载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53页。
[66]详见前引[10]]Isensee书,第106-121页。
[67]Schneider/Ehmke, VVDStRL 20(1963),S. 1,50 und 53,73,102, die Verfassung sein auf materiale Prinzipien hin auszulegen.
[68]许宗力:《宪法与政治》,载许宗力:《宪法与法治国行政》,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二版,第23页。
[69]BVerfGE 34,1,14 f.
[70]参见黄舒芃:《“功能最适”原则下司法违宪审查权与立法权的区分—德国功能法论述取向(funktionell-rechtlicher Ansatz)之问题与解套》,载《政大法学评论》第91期,第99页、第127页以下。该文指出,“功能法”取向强调的是“功能最适”的权力分立原则,但仍然无法解决具体情况下如何判断究竟何者“功能最适”的问题。
[71]Hassemer, Politik aus Karlsruhe? JZ 2008,S. 1
[72]Hassemer, ebd.
[73]Luhmann, Rechtssystem und Rechtsdogmatik, 1974, S. 7.
[74][德]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49页、第355 -356页。当然,阿列克西的理论总结是否完全覆盖了普遍实践论述在法律论辩中起到作用的所有情况,仍待求证—尤其相对于宪法解释而言。也许正因如此,阿列克西才使用了“可能是有必要的”之表述。
[75][德]施莱希、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76]BVerfGE 8,38,41.
[77]前引[5],边码58。
[78]BVerfGE 1,14,32.
[79]对此,有学者提出,联邦宪法法院的审查权构成了对议会主权的事实上最为重要的限制。参见Fleiner/Fleiner, Allgemeine Staatsle-hre, 3. Aufl. 2004,S. 434 f.。
[80]Vgl. BVerfGE 93,121,151 f.-Sondervotum Boeckenfoerde.
[81]联邦宪法法院进行自我克制的目的在于限制法官的审查行为。具体而言,其目的并不是要削减宪法法院的权限,而是要使法院放弃“从事政治活动(Politik zu treiben)”。换言之,联邦宪法法院不应介入宪法为政治上的形成自由权所预留的空间。参见BVerfGE 36,1,14 f.。
[82]前引[7], Badura书,边码A 14。
[83]基本法第79条第1款、第2款对于立法机关修改宪法的权限和程序作出了具体规定。同时,该条第3款规定,立法机关对于宪法的修改不得违背联邦国家的组成和基本法第1条至第20条中规定的原则。因此,基本法第79条第3款同时又构成了对于立法机关权力的限制。
[84]Ossenbuehl,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Gesetzgebung, in: Badura/Dreier(Hrsg.),FS 50 Jahre Bundesverfassungsgencht, 2001,BandI, S. 33.
[85]Schultze-Fielitz,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in der Krise des Zeitgeists. Zur Metadogmatik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ation, AOeR 122(1997),1,10.
[86]前引[15],第1章边码57。
[87]前引[9],第203页。
[88]相同的观点参见张嘉尹:《宪法解释、宪法理论与‘结果考量’—宪法解释方法论的问题》,载刘孔中、陈新民主编:《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践》第三辑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2年版,第5页。
[89][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90][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6页。
[91]Haeberle, Die offene Gesellschaft der Verfassungsinterpreten, in: JZ 1975,297 ff.
[92]Haeberle, ebd.
[93]前引[40],第90页。
[94]前引[40],第90页。
[95]Mueller, Juristische Methodik, 2. Aufl. 1976, zitiert aus Schlink, ebd.,S. 91
[96]Schultze-Fielitz,前引[85],第4页。当然,在舒尔泽—菲利茨之前,早已有学者注意到了此现象,例如阿多梅特提出:“对于每一个……裁判而言,人们都可以设想出一个意见相反的裁判,而后者也能够得到解释方法上的同等程度的论证。”S. Adomeit, JZ 1980, 344.
[97]V. Danwitz, Quelifizierte Mehrheiten fuer Normverwerfende Entscheidungen des BVerfG?, JZ 1996,481,484.
[98]前引[33],第340-341页。
[99]前引[73],第31页。
[100]前引[46],拉伦茨书,第222页。
[101]前引[46],拉伦茨书,第237-238页。
[102]前引[26],第160页以下。该学者同时指出,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还有Engisch, Larenz, Coing等。学者张嘉尹将结果取向定位于“从属于目的论论证”,所持的也是基本相同的观点,参见前引[88],张嘉尹书,第26页。
[103]前引[74],阿列克西书,第298页。
[104]BVerfGE 34, 269, 287.
[105]Maunz/Zippelius, Deutsches Staatsrecht, 29. Aufl. 1994, S. 43.
[106]Vgl. Jescheck, Strafrecht AT, S. 138 f.
[107]前引[26],第173页以下。
[108]前引[75],第44 -51页。时至今日,在德国的十六个联邦州中,仅有巴伐利亚和萨尔两个州规定了宪法法院法官必须由法学者担任,其他十四个州并未作出同样的规定。
[109]前引[71],第4页。
[110]前引[5],Hesse书,边码76。
[111]前引[46],拉伦茨书,第222页。
[112]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113]范进学:《对话商谈与方法多元—论中国宪法学研究方法》,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20页。
[114]较典型的如郑贤君:《宪法解释是政治法律化的根本途径—兼议司法释宪的形式化特征》,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
[115]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第502页。
[116]范进学:《宪法解释主体论》,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6期,第41页。
[117]苏力:《面对中国的法学》,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3期,第3页。
[118]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兼论法学家在推动宪政中的困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25页。
[119]韩大元、张翔:《试论宪法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第45页。
[120]前引[33],第334页。